令人兴奋的特币
-
「比特币令人兴奋」 一个刚出狱黑客的自白
2013 年,丝绸之路创始人 Ross Ulbricht 被捕入狱。经法院审判,他犯了贩毒、协助和教唆通过互联网分销毒品、电脑黑客和洗钱等罪行,被处以无期徒刑,不得假释。虽然距离被捕已经 7 年了,Ross 仍在社交媒体上「活跃」,试图获得更多声援、寻求减刑。
「加密货币」是 Ross 表达狱中感受外,另一个关注的话题。虽然身处高墙之内,Ross 曾对比特币给出「3000 不是底,10 万不是顶」的预判,今年 6 月,他还发表了一篇长文,详述了自己对 DeFi 协议 MakerDao 的思考和展望。
但 2500 天的隔绝生活,已经让这位曾一手创立丝绸之路、缔造了一个黑暗帝国的黑客,脱离了加密行业一线。
实际上,即便是当初在互联网中来去自如的黑客,因为恶行被捕入狱后,也不得不面临彻底「断网」的窘境。数年的监狱生活,最终让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,陌生和隔阂,基本是这个群体出狱后的感受。
据了解,Ross 的推文并非他直接发布,而是通过家人或朋友间接的「传话」。如果 Ross 还有可能出狱,那 Jesse McGraw 今天经历的事情,估计会是他明天的遭遇。
前不久,一名入狱十年的黑客 Jesse McGraw(又名 GhostExodus),出狱后发表了一篇长文宣泄自己对当代社会的陌生感,以及十年牢狱对他的可怕影响。他不仅无法理解触屏智能手机的使用方式,包括他当初熟悉的 Windos 系统,在多次迭代后,也已经让这位昔日的黑客组织创始人,无从下手。

不过,在初步了解这个新世界后,深入骨髓的「黑客敏感」还是让他意识到,比特币的不同之处,他在文章最后特别将比特币的出现列为第一个让他倍感兴奋的事物。
Jesse McGraw 出狱后,他发表了一篇文章,详述了自己的狱中点滴。通过这篇文章,我们大概能想象,和 Ross 一样的黑客在犯罪被捕后,狱中的类似经历。以下是 Jesse McGraw 自述,原文链接在文末。
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。
当初,我因为在一些医院系统上安装僵尸网络和商业远程访问程序而被捕,其中包括一个关键的 SCADA(监控)系统。我成了美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因破坏工业控制系统而被定罪的人。虽然在很多人看来,这已经很久远的事情了,但对于我来说,恍如昨日。
十年噩梦
你很难明白在美国当一个囚犯意味着什么。目前,大约有 230 万人被监禁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,监狱并不会囚犯提供十分便利的上网权限,想要获取信息,只能通过阅读或者观看监狱批准的报纸、杂志、出版物或者电视节目。
当然了,大多数囚犯其实可以使用电脑,但监狱提供的电脑设置了一种特殊的访问控制程序,囚犯要想使用电脑,需要支付每分钟 0.05 美分的费用,而且电子邮件只能发给监狱批准的联系人。但是,黑客在联邦监狱里混的并不怎么好,通过囚犯信息系统与公众接触并不是我所能拥有的特权。
2011 年夏天,我想要上诉。但因为被各种限制,我甚至都没有办法联系律师,所以私底下,我和另一个犯人达成了协议,他给我使用他的电脑,这样我就可以收发电子邮件了。
不过最终我们还是被发现了。这名囚犯被监狱的特别调查部门 (SIS) 逮捕,原因是他的电脑信息账户最近有一系列的异常活动。而我姐姐在回复的邮件里提到了我的名字,于是 SIS 也知道了我是这系列活动的幕后推手。
这位狱友不仅没有说明情况,还直接「反水」了,他说自己不知道我在用他的账户,自己的账户是被我给黑了。

Jesse McGraw每年提交表格,申请恢复电子邮件特权
之后,我在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,就在一个行政隔离部门拘留了13个月(律动注:Ross Ulbricht 自述也曾被关押于暗无天日的专门的隔离房间),这个案件也被移交给了联邦调查局。有些人把这些设施称为“黑色场所”,因为它们会让被关进去的人与媒体、访客和律师完全切断了联系,大家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。
狱中的生活苦不堪言,一周洗三次澡,人被限制在一个8X10平方米的囚室里,没有空调,没有风扇,也没有足够的通风。有一年夏天,我房间里的温度达到了华氏125度(约51摄氏度)。没有任何证据支持那个狱友对我的指控,我希望回到普通牢房中,但我期望的事情并没有发生。
你能想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,我无法接触到当下时代的任何信息吗?
走出时光机,重返现实社会
在服完漫长的刑期之后,出狱后的我在亲眼目睹科技的发展后,感觉自己就像从时间机器里走出来一样。
我感觉自己被时间抛弃了,被新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社会的发展驱逐了。作为一名黑客,我是名为“Electronik Tribulation Army”黑客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。我过去常常与最新的玩意、开发和社会技术趋势保持同步,还常常对恶意软件进行反向工程,执行事件响应,并侵入几乎所有无人关注的东西。
当然,在服刑期间,我也在报纸和杂志上读到了一些新科技内容,但说到底,我现在是一个外人了,一个对我曾经熟悉事物的局外人。如果你只是把这件事形容成老师变成了学生,只要重新学习就行,未免太轻描淡写了。
不适应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比如最近,我收到了一台新的戴尔 Inspiron 笔记本电脑,打开熟悉的包装,摸着它的感觉就好像是他乡遇故知,但当我启动它,迎接我的却是 Windows 10。对于我来说,Windows 7 beta 版的发布,仿佛就在昨天。我对 Windows 10 一无所知,完全不会使用。它有一个新的文件系统,但我对它如何工作一点也不好奇。我想要做的,只是让我的 Windows XP 恢复到原来的 Ubuntu Linux 和 Backtrack 3 双启动选项。
Windows 在系统控制的话语权上,比我更胜一筹:我不再能像以前一样流畅而顺利的操控这个系统了,我现在很讨厌它。我花几个小时在谷歌上搜索如何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,而往往又是无功而返。我一次次挑战这个讨厌的系统,再被一次次的打败。
还有一些事情,让我难以接受。比如我不得不问我 12 岁的女儿,什么是 # 话题标签(hashtag),这太让人尴尬了,「你不应该是个黑客什么的吗?」她对我说,这句话给像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这十年里,很多事情都变了。
在我那个时代,雇佣黑客被认为是一种禁忌,而现在,谁都可以雇佣黑客,甚至白帽黑客还可以通过发现漏洞获得奖金,这些钱是合法收入的来源,也使白帽黑客已经成为一种职业。黑客们甚至在好莱坞电影、书籍和视频游戏中被大肆渲染,诸如「Mr. Robot」这样的黑客,在美国电视网络中被描绘成了英雄,不再是老套的网络恶棍。
一个我不再觉得与之有联系的世界
当我还在对过去熟悉的事物念念不忘时,世界却在突飞猛进地前进。其实,我也在这个令人兴奋的新世界之外观察到的一些事情:
比如比特币,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种加密货币,但我仍然不确定如何获得或使用它们。
2007 年智能手机出现,两年后开始取代翻盖手机,当我在电视上看到智能手机广告时候,我对着电视大喊「这是最愚蠢的事!谁愿意把油腻腻的手指放在屏幕上?」但我错了,每一个人都会这么做,包括我。再比如,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项紧急控制互联网的行政命令,互联网的「死亡开关」由此诞生。这也是一件大事。
对于我曾经熟悉的互联网世界,随着 Arab Spring 到来,社会意识开始转向使用 Tor 等工具和加密通信平台来保持互联网的匿名性,端到端加密通信开始流行起来。社交网站 Myspace 陷入了深渊,结束了我所知的那个建立个人文件创造的时代,功利主义似乎已经是当今世界的默认理念。
比如 ZeuS. SpyEye. BlackHole 和 BackSwap 这样的银行业特洛伊病毒也流行了起来。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上,可用的 IPv4 地址估计很快就要耗尽了。
一等兵切尔西·曼宁 (Chelsea Manning) 泄露大量美国国务院敏感电报之后,维基解密运动爆发了。黑客组织中的「匿名者」成为支持这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;爱德华·斯诺登(Edward Snowden)后来成了告密者,他向记者泄露了 9000 至 10000 份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绝密文件,曝光了一个名为「棱镜」(Prism) 的庞大间谍项目。美国政府仍在进行间谍活动,它一直会这样。
大型广告商正在收集用户的各种数据,以达到内容营销的目的。以前我也曾经窃取过用户的数据。我知道这么做违法,如果不是的话,我估计也给他们发一两个广告。
Facebook 和谷歌已经根植在网络用户的日常活动中,智能手机和汽车越来越受欢迎,当所有相互连接的设备都无线连接到一个命令和控制设备上,这无疑是黑客的战场。亚马逊的虚拟助理 Alexa 可能是一起谋杀案的目击者,这些 AI 软件一直在倾听和记录你的生活。
不确定的未来
对刚出狱的我来说,就像是踏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。
我再也看不到有意义的人际互动了,这个社会被喜欢、自拍、智能手机和类似的技术搅得心烦意乱,在新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常常让我感到沮丧,因为我没有跟着世界一起「进化」。我像是在时间之外的某个地方,镜子的另一边等待,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释放,重新融到社会中,我已经不了解面前的这个世界了。
- 数字货币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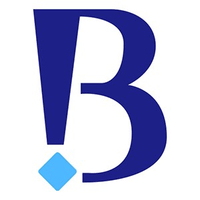





 4247167
4247167 





